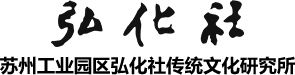编辑◎仁嗣 超明
【编者按】2011年9月9日,记者专程前往河北邢台玉泉禅寺,就当前教界关注的佛教教育、寺院管理、文化建设等话题向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净慧长老进行了请益,长老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慈悲开示,可谓振聋发聩,给我们当代佛教的发展以深深的启示。
记者:师父慈悲,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拜访您,并就当前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对您做一次专访。2000年初,您即积极投入佛教教育事业,出任河北省佛学院院长,并组织全国的专家学者编写佛教教材。您认为,什么是佛教教育,这个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净慧长老:佛教素来重视教化、重视教育,这是与佛教同时存在的问题。佛教的本身是要起到教化的作用,“化”是改变,着重在转化。现在新的名词是教育,“育”则着重在培养。从小到大,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后,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是让人从小孩到成人受培养的过程。这一种培养方式称作“教育”比较合适。
而佛教教育所针对的以成年人为主,从目前的宗教政策来讲,年龄在十八岁以上才是成年人,出家的一般都是成年人,所以佛教是通过传教的方法来改变受教化者的人生,改变其努力的方向、发展的方向,所以佛教强调的是“教而化之”。“ 佛教”两个字本身就包括了佛陀的教法与接受教化的人在理论上的认识,在实践上的修行,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佛教的意思。有大德讲佛教是教育,这样的强调有点过分。佛教就是佛教,佛教重视教育,这是它已有的内容之一。自古以来,僧人的职责——“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弘法和利生是同步的。
佛教教育在过去是以禅堂教育为主的,以老师和学生进行“个人对个人”的教育为主要方式。像现在这种集体的教育,在佛教中很早就有这种形式,比如说法师讲经有很多人听,虽然不是固定的,但它也是一种培养人才的方法。到了明朝晚期,憨山大师在广东南华寺,把沙弥集中在一块,除了自己讲课,也请一些在家的老师来讲课。既讲普通的知识,也讲佛法。普通的知识当时是以儒家的学问为主。当时的学问比较专一,没有我们现在的学问这么广博。所以他们能够只读儒书、佛经就可以了。到了清朝末年,才慢慢有了接近现代教育的僧伽教育出现。这个历史大家都很了解。
作为佛教教育究竟应该怎么办,注意哪些原则,我们河北省佛学院提出了四个字,叫“信戒学修”,它的目标就是培养一个和尚,培养僧人的僧格,也就是僧人的资格、僧人的人格。僧人作为一个教化者,必须要有这个资格。以“信戒学修”这四个字作为佛教专业课程的根本目标,与此同时,政治上要热爱祖国,爱国爱教,这些内容都是必须要有的。从一个出家人来接受佛学教育的角度来看,则必须要坚持“信戒学修”这四条。
僧格能否完成体现在修上。学是为了修,信是为了修,戒还是为了修,把信戒学三者纳入到修的范围之内,再来进行教化,如此一来,作为僧人教育就可能不会出现偏差。否则的话,只是强调讲经说法等佛学知识的培训,打禅七没有?打佛七没有?这是一个根本的缺陷。作为出家人,僧格的核心内容,是对佛法的实践,作为僧人,只有取得了“信”、“戒”、“学”、“修”四个方面的成就,你才可以算是初步有了僧格。
记者:学修一定要一体化。
净慧长老:对,一体化。所以我们河北省佛学院倡导的是以“信戒学修”为内容,以“养成僧格,融入僧团”为目标的僧伽教育。首先学僧来这里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养成僧格。养成僧格体现在何处?就在于能不能融入僧团。不能融入僧团,培养出来的僧人不过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佛教学者,不能融入僧团就无法住持佛法。所以说,具足“戒定慧”三学可以作为养成僧格的目标。实践六和的精神可以作为融入僧团的目标。我们现在的佛教教育实际上就是僧伽教育,而僧伽教育肯定是培养僧人的僧格,能够在僧团带领四众走爱国爱教的路,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这是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兴办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
现在不是缺乏学者,而是缺乏真正具有僧格的僧人,能够带动僧团的僧人。一定要把这个目标搞清楚。说白了,佛学院就是要培养和尚,培养一批合格的和尚。一定要把这个目标亮出来,你才能大胆地说话。那些真正想当和尚的人,他可以来接受这个教育;那些不想当和尚的人,他可以接受别的方式的教育。佛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合格和尚,没有第二个目标。
现在不敢说这个话,培养弘法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人才,培养能够当方丈的和尚,培养能够讲经说法的和尚都能提,就是培养和尚“养成僧格,融入僧团”这个八字方针不敢提,这就无法贯彻佛教教育的根本宗旨,结果是菜篮子打水一场空。所以,佛教教育,核心要把握,这个八字方针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
记者:那当前的佛教教育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净慧长老:现在大概全国各个佛学院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佛学院中,出家人的老师,不能够带动学僧过僧团生活,带动学僧来实践佛法、修证佛法。这一条解决了,学僧能够跟着老师上殿、过堂、坐禅,佛学院就能稳定,佛学院“信戒学修”的人才就能够出现。用儒家的观念来讲,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现在的老师顶多也就是在“授业”而已。“传道”没有,“解惑”更没有,下了课各人就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了,跟学生不见面。必须把“传道、授业、解惑”这三者在每个老师身上落实了,佛学院才会有好的老师出现,有了好的老师,就一定能够带出好的学僧。要做这样的老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的老师必须是天天要陪着学僧,一年到头要陪着学僧。所以佛学院的学僧不宜太多,规模不宜办得太大。几十个人,多一点老师,就能够出好人才。培养学生,从社会到宗教界,出现的问题都是老师不能带动学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生活上完全脱节。老师完全不能够起到表率作用。只有言教,没有身教。老师没有身教,他的威信就树立不起来,他说的话就没有含金量。你说的话,你自己怎么不去做?你都不做,凭什么叫我们做?你说的话有什么含金量?没有含金量的话有什么作用呢?师资力量一定要紧密结合起来,从教学到修行到生活,都要跟学僧打成一片,这样做一定能够培养出好的学僧出来。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
老师们只是在教书,没有在培养人才。
老师只是把那一节课讲完就算了,学生消化了没有?不知道。
学生是不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止观去修?不知道。
学生是不是在按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做?不知道。
这些你都不知道,你教的学僧有什么用呢?就好比农业大学的学生,老师将学生亲自带到稻田里去,这是草,这是稻子,稻子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这些都需要告诉他们。现在佛学院的教育就是教与学脱节,师生不能打成一片,老师不能在修行上起表率作用,只注重言教而缺乏身教,这样对学僧没有影响力,学僧没有一个可学的表率。
历代的高僧,都是依止着他的师父,由师父培养出来的,师父怎么教,徒弟就怎么学,这就叫做传承。历代的高僧都是这样,老师是什么样,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什么样。
记者:现在一些社会大学,如北大、人大、南大等都有相应佛教类的研究机构,像柏林禅寺也经常和国内很多高校有佛教相关的交流。您认为,现当代社会大学有关佛教研究和教育的方法,对佛学院的现代化教育有什么启示和借鉴作用?
净慧长老:我觉得,社会上的大学研究佛教与我们佛教界研究佛教、学习佛法,二者具有不同的目标。它们的方法,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借鉴,不能照搬;它的经验我们也只能有选择地去吸取,因为它不是在培养信教的人。我们则是在培养信教的人。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信戒学修”这四种精神的人,是要培养“养成僧格,融入僧团”的人,是要培养和尚,他们不是这个目标。
佛教教育还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在政治上也就两条要求——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可以了。所以社会大学的教学方法和经验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借鉴,不能照搬,这是一条。第二条呢,社会大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信息,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完全照搬。
因为我们的僧伽教育是以信仰为中心的教育,不是以学术化为中心的教育。信仰与学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冲突的。现在强调佛教学术化的这个口号,不完全正确。
我感觉到,我们佛教教育,培养信仰,对当前稳定佛教教职人员队伍来说,这是关键。现在这支队伍并不稳定,而且不纯洁。这支队伍不纯洁,佛教的教化作用就要打折扣,党和政府对宗教教职人员的四条要求就很难落到实处——政治上靠得住,学术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候起作用。一定要在“信戒学修”上下功夫,不在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僧伽教育也就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不会有实际的效果。表面文章做一做,最后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党和政府依靠不了这样的人,佛教更依靠不了这样的人。大家是恨铁不成钢。希望佛教界多出几个高僧,并且能在国际佛教舞台上叫得响。这样的高僧太少了。
记者:您认为,高学历与佛教修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净慧长老:我感觉高学历与佛教信仰之间是没有矛盾的。现在也有几个高学历出家的人出家修行,一般的人还是赶不上他们的道心。这里的关键是扎根要正,出发点要正。柏林禅寺有一个高学历僧人,北大出身,叫明海。他不但在学校里是高学历,出家后还是非常注意学习,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但是他的信仰是一般人赶不上的。他每天上了早殿、过了堂,就读《金刚经》,每天如此。直到他当了柏林禅寺方丈以后,仍然如此。他觉得自己的修行和现在所处的位置不相衬。学问有一点,但是修行跟不上。所以他坚持要去闭关三年。河北省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很支持他。对自己严格要求非常不容易。从明海来看,高学历和信仰之间是没有冲突的。
但是如果在佛学院里用佛学学术化的方法去培养僧才,那肯定是培养不出来有信仰的僧才的,这种方法只能使信仰一天天淡化。关于信仰淡化程度,“文革”以后和“文革”以前是不大相同的。信仰的淡化自然和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同时也和佛教内部所强调、传播的某些思想有关。我觉得信仰淡化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我要强调“信戒学修”,佛学院的教育要以培养、提升学僧的信仰为核心。
记者:当前,国家宗教部门强调出家人要以讲经说法为家务事,您认为,该如何培养出家人的讲经说法能力?
净慧长老:国家宗教部门强调培养出家人讲经说法的能力,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都能够对自己所信奉的教理教义作出符合时代要求、时代进步的阐释道理是一样的,我想这是宗教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作为佛教的讲经说法,怎么样提高这种能力,恐怕还得走传统的老路。首先由老师讲经,然后十个、八个学生来听,不能多了,多了肯定是培养不出来。十个、八个学生来听,听了以后,比如老师讲了一座,下边的学生抽签,覆小座,就是你重新讲一遍。再比如说有二十个学生,二十个人都进行准备和复习。然后不能是二十个人都讲一遍,得抽签,抽到谁就是谁讲。准备可以都准备,复讲就只能一个人讲。这种方法大概用了几百年、上千年了。覆小座,佛教有这个传统。这个方法不管怎样,老师讲经的那种风度、那种方法,甚至那种思维模式、讲经的姿态,你可以学到。而且你在覆小座的时候,不但有你这二十几个同学在听,同时老师也是在旁边听。每个人在准备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还有第二种方式,比如说请一个法师来开大座,然后又请一或两位法师来作辅导。老师这课讲完了,下午你就再辅导一次,把老师没有讲到的地方,或者是讲了,听众还没有听明白的地方,再讲一次。当时学,当时讲,很容易记住。我想,这不是培养讲经能力的唯一方法,但仅仅靠现在课堂的这种办法,要培养讲经的能力也不大容易。
再就是,要鼓励健在的老法师,真正是科班出身的,按照传统讲经的办法,示范性地讲一两部经,然后把它录成带子,有意识地来推广这种讲经的方法。我们要想发挥经文的要义,首先对经文本身的原意是什么,要有个系统的了解,然后才可以找到某一点来加以发挥。首先是一种基本的培训,技能的培训。讲经就完全成了一种能力,没有基本的技能培训,讲经的能力是无法形成的,覆小座就是一种技能的培训。
李炳南居士写过一本书——《内典之研究》,这本书的章法就可以学,我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我们讲经的一本教材,可以专门就这本书来培训一批人。他起码知道这个章法,知道一些技巧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们是没有这个技巧,没有这个章法。再就是,开大座讲经没有了。请某个法师讲经,仅仅是听他谈体会而已,都是讲他自己的东西,不是讲经文。
记者:您认为,佛学院应该有怎样的筹划,才能培养出在管理、弘法等方面适应现代佛教发展的合格人才?
净慧长老:这个牵涉到佛学院必须要依托一个僧团来培养来办佛学院的问题。他既是佛学院的学僧,又是僧团僧人的一员。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真正融入僧团。融入僧团以后,僧团的管理,可以慢慢了解。现在寺院工作无非是接待(全国的大寺院都忙于接待)。接待工作如果做得好,也不失为个人锻炼的一个好机会,同时也是传播佛法的一个重要渠道。只有认识这件事的重要性,才能够起到这种作用。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我在佛教事业方面,有许多的因缘都是与做接待工作分不开的,在做接待工作当中,就创造了许多有利于推动佛教事业,推动寺院发展,扩大佛教影响的因缘。同时,作为一个出家人,在接待工作中,可以认识很多人,积累一些人际关系,这还是很有意义的。
当前来讲,管理无非是接待。外事,有外事接待;内事,有内事接待;信徒,有信徒的接待;政府官员,有政府官员的接待。在接待工作当中,如何立足本位,这点很重要。这是个关键,就是不能错位,过去叫做在教言教,作为和尚,应立足于和尚的本位、佛教的本位。这就是讲我们做接待工作的,它的中心是什么。接待工作,比如说接待外宾,过去陈毅讲过一句话,“接待外宾,阿弥陀佛加友谊”,那也是在教言教。
在管理上,怎么样锻炼能力,就是说佛学院不能够脱离僧团,一定是要让佛学院的学僧,最起码的,寺院各个寮口执事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要了解,要熟悉,要实习一遍。在读书期间,两年也好,四年也好,你必须与僧团结合在一起,僧团做什么,学僧也去做什么。这就是锻炼学僧毕业后融入僧团,有管理的能力,甚至有当住持的能力,有当会长的能力,那都是从很小的事情慢慢学起的。
我们佛学院,培养的人,“养成僧格,融入僧团”这八字方针,你学了之后,首先要讲得出来,要写得出来,要唱得出来,要做得出来。和尚不会唱念也不行,你作为一个教职人员,你不懂这个不行。不是为了赶经忏,但是殿堂佛事还是需要有唱念。“做”包括修行,能够打坐,念佛,参禅,都能做得出来。
记者:刚才师父谈到寺院管理,二十几年来,您先后主持柏林寺、黄梅四祖寺、当阳玉泉寺等寺的恢复重建工作。就您几十年来所积累的寺院管理工作经验而言,您认为,管理好寺院的法钥是什么?
净慧长老:就像现在我住持的玉泉寺就不需要规矩,都是大家做就完了。这个管理要实现的,就是没有管理的管理。只有实现了这个,你才可以真正叫做是个僧团。僧团他本身是个没有管理的管理。既不要惩罚,也不要人喊叫,什么法器一响,他就晓得干什么。
所说的法钥,不敢当。我的经验很简单,就是“两爱、双风、四要、四不要”,一共九个字。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坚持两爱的根本方向,树立双风的根本任务。根本方向就是坚持两爱——爱国爱教,树立双风——学风、道风。这是纲领,是根本,只要把这个根本抓住了,纲举然后就目张。爱国怎么做,爱教怎么做。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概括的四个维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做到这四条,就是爱国的具体要求。如果再把它具体化,就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守法,这些要求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够脱离大方向,脱离大方向,脱离了爱国,也就谈不上爱教。因为爱教是在爱国当中体现出来的。教有没有尊严,有没有威望,今天来讲,就看爱国的根本方向是否坚持了。在爱国的大方向上出了问题,任何一个教,全国人民都是不欢迎的,全国人民不欢迎的教,你能起什么作用呢?所以说这个大方向不能动摇。这是根本方向,根本任务。就是要树立双风——学风道风,这两点是我们学佛的人的一种基本要求,基本修养。学习佛法,在家信徒也好,出家信徒也好,要懂得基本的教规教义,要懂得基本的实践方法,要有一个修行的法门,你才能够将所学的东西跟实践结合起来。然后是具体到怎么样来落实爱国、爱教,怎么样落实学风和道风,那就要在四要上体现。
四要,第一是寺院的道风一定要传统化。如果脱离了传统,就脱离了信教群众的要求。信教群众总希望寺院要传统一点,僧人要传统一点。所谓传统包括学风建设和道风建设两个方面,学风要传统,道风更要传统。虽然只提了道风建设,但是也包括学风在内。
第二是寺院的管理要律制化。律制,律就是戒律,制就是清规。中国从佛教传入进来开始,在戒律上走的就是双轨制的道路。戒律能落实的,我们尽量落实,戒律不能落实的,我们另外制定一些落实戒律精神的规矩,一直到唐朝形成了《百丈清规》——丛林清规。这是双轨制,清规和戒律双轨制。所以寺院的管理一定要律制化。
第三是寺院的弘法要大众化。佛教一定要普及到大众当中,佛教才有基础。佛教面临的形势是四面楚歌,岌岌可危。弘法不走大众化的道路,佛教的阵地越来越小,信教群众越来越少,这既不是佛教所希望的,更不是宗教政策所希望的。佛教的影响能够扩大点,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维护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的形象,所以弘法一定要大众化。弘法不仅仅是讲经说法,包括寺院举行的一些活动都要面向群众,不能只面向少数人,也不能只面向富人,要面向老头、老太太。你要知道老头、老太太们代表的是他一家人,一般地来讲,老头、老太太到寺院里来,都受到儿女的尊重,都受到子女的嘱托。比如说,来寺院要求菩萨保佑,要生个孩子,要发财,要没有病,这些朴素的信仰,是佛教高层信仰的基础,没有这些朴素的信仰,更纯的信仰不可能有,还是要尊重这种朴素的信仰。有这种朴素的信仰,比较纯粹的佛法信仰才有传播的基础,否则的话,一点认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怎么给他传播佛法呢?所以,不要忽视老头、老太太,老头、老太太他是一家人的全权代表。所以寺院弘法要大众化,当然,也要适当地为年轻人举行一些活动,比如我们每年举办的夏令营和节假日的共修,这些不光是局限于老太太,基本上是为年轻人举办的。每个寺院要坚持不懈年年办活动,活动是固定的。不是说办了一次,第二次没有消息了。宗教政策对宗教活动场所的定位是,满足广大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不只是为出家人开放的,是要面对广大的信教群众的。所以说,弘法大众化,这是和宗教政策相吻合的。
第四是寺院的生活要平民化。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现在有些寺院的生活有一点超标,寺院的生活超标对于佛法发展的前途来讲极为不利。我们学习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历代的“法难”,多数是由僧侣生活的腐化而引起社会的不满。所以,我们僧人要自觉地过平民化的生活,这是维护佛教正法久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措施。
然后是四不要。做人不要有俗气,做事不要讲阔气,现在讲阔气、讲排场之风越刮越凶,动不动就几千人几万人搞庆典活动,动不动就是请108位高僧举行开光。这些东西还是少搞为好,太讲排场了不好,我们不要去赶潮流。处事不要有官气,待人不要有霸气。“俗、阔、官、霸”四气,我在中国佛教协会一次会长扩大会议上讲过一次,好像《法音》上都刊登过,有些反响。现在我们强调要加强道风建设,强调提升佛教整体素质,把“四要、四不要”做到了就行了。“四要四不要”讲清楚了,道风建设就有内容了,否则的话,道风建设没有内容。在寺院管理上抓住“两爱、双风,四要、四不要”这个纲,大方向就不会错了。当然具体的管理办法,各个寺院因事因地都有不同的规章制度。“ 两爱双风、四要四不要”是寺院管理的大框架。
记者:您认为,如何使传统的丛林规约与现代管理制度有机结合?
净慧长老:我觉得传统丛林的管理体制,和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有不谋而合之妙。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分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这三个层面,传统丛林也是这样:决策层是方丈和班首;管理层是各寮口的执事;执行层是管理层的副职,他们负责执行。
记者:“丛林要学院化,学院要丛林化”,这样的设想是不是适合现在的佛教发展呢?
净慧长老:刚才讲的时候,我就讲到,一个佛学院一定要依托一所寺院来办,这就是想使学院能够丛林化,只有学院丛林化了,“养成僧格,融入僧团”才真正能够具体落实。像现在的佛学院完全是照搬社会学校的办法,这不一定是非常好的选择。在今天信仰极为淡化的形势下,按照社会学校的办法来办佛学院,放寒暑假无疑就是鼓励学僧脱离僧团的修持生活,脱离佛学院的学习生活。暑假两个多月,寒假差不多一个月,一年中有一个季度脱离僧团,脱离学修生活,这对僧才的培养、信仰的养成、修持的落实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这种放假制度首先要取消,一定要按照丛林的规矩,冬参夏学。
河北省佛学院学僧放寒假就参加常住打禅七,尽管这么坚持,还是有一部分学僧不肯参加禅七,要回去。佛学院不抓修持,有学有修的人是培养不出来的。
佛学院学僧的寒暑假怎样安排更有利于僧格的养成,信仰的提升,学业的成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形成共识,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利于佛教教育健康发展。
记者:如今,寺院硬件建设已得到恢复,您认为,软件建设——寺院的弘法功能方面,将如何得到提升以适应现代人的信仰所需?正如您在《从佛法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创建》中指出的,要积极引导公众讲信仰、讲因果、讲良心、讲道德、保住最基本的伦理底线,您能进一步阐述一下吗?
净慧长老:我现在也感觉到,我提出的这些理念应该说和佛法总体精神是吻合的,和现在时代的需要也是吻合的。“信仰、因果、良心、道德”做人的八字方针,我们这个时代尤为需要。现在我感觉到软件建设方面,从全国的佛教界来讲,各个寺院自身要从传承宗风入手,找准自己的位置,要定好位,要抓住所在寺院的宗风是什么,没有宗风的传承,就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找不到指导寺院长期发展的核心理念是什么。一座寺院没有一个核心理念,开展活动就会有盲目性。
柏林禅寺从1991年开始就提出了“生活禅”的理念。这是在赵州禅、临济禅的基础上使禅宗现代化的一种具体实践。其他的寺院,天台宗有天台宗的宗风,净土宗有净土宗的宗风。从我的观感来看,庐山东林寺在发扬净土宗的宗风方面做得不错。他们真正把净土宗的要领抓住了,方法掌握了,然后具体地运作起来,从硬件上加强建设,从软件上加强落实,一心一意弘扬念佛法门,坚持信愿行,弘扬净业三福[1],这都是很契时机的。这些理念,既可以作为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基本纲领,也可以成为社会人士做事的目标。结合社会实践,信愿行也可以成为企业理念,文化理念,而净业三福更具现实意义。每一座寺院,不管是弘禅、弘净、弘密,能够把自己的宗风找到了,然后有一个理念,根据这个理念来展开弘法工作、接待工作、管理工作,就能够有目标,就能见成效。
[1]净业三福:语出《观无量寿经》,即指“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之三条。
记者:您如何看待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否有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二者之间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建设与协调?
净慧长老:在我看来,在今天山林寺院比城市寺院更重要。山林寺院具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具有山林自然风光的优势;再一个,如果山林寺院管理好、学风好、道风好,它就有吸引人的地方。而城市寺院首先没有风景;第二,学风、道风建设的难度肯定比山林寺院大得多。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山林寺院更具有发展优势。从弘法的受众来讲,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城市,今天还到城市寺院去,有些人会感觉没有什么必要,还是到山林寺院去。现在是双休日,山里面住两个晚上,大多数人都是有车族,山林寺院更加有优势。城市寺院要管理得好,难度更大。
记者:您亲任主编,公开出版《虚云和尚全集》。在您的主持下,河北省佛教又出版《中国禅学》、《禅》及《正觉》等期刊。于此,在佛教文化建设方面,您认为,如何看待佛教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在当今时代,如何使佛教文化建设得到政界、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净慧长老:佛教文化是佛教的一个载体,或者说是一种体现,所以佛教文化工作在今天来讲,特别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佛教与佛教文化,不是两回事,就是一回事。但是在当今的佛教发展上,如果能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理念来做佛教文化的话,则更容易引起政界和学界的认可和共鸣,如果我们老是陈陈相因,老是炒现饭,老是在低水平上重复,这样学界肯定不乐意参与;政界呢,他觉得做出来了,当地的佛教界甚至于宗教部门的工作也找不到一个亮点。所以说如何使佛教文化工作,做得有亮点,这恐怕是取得政界、学界认同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个亮点也不是凭空的杜撰,要找到一个地区的佛教文化资源是什么,这个亮点要从佛教文化资源里面去找它。比如说我们在河北开赵州禅、临济禅、生活禅的三禅论坛,别的地方可不可以重复呢?看起来不可以重复的。因为赵州禅在河北,临济禅在河北,生活禅也首先在河北提出。各地有各地的文化资源、文化底蕴、文化传统,只有结合了当地的佛教资源来做佛教文化,才能丰富地方的文化宝库,丰富社会的文化资源,丰富佛教的文化内涵。我在河北重点是弘扬赵州禅、临济禅,但我到黄梅去了,我就不能唱这个调了,到黄梅去了,我是突出禅宗的四祖、五祖、六祖,他们原来把六祖忘记掉了,我说不要忘记六祖,忘记六祖,四祖、五祖的意义就减分了。正因为有了六祖,四祖、五祖才更有光彩。黄梅是四、五、六,要把四五六祖捆绑在一起,黄梅的禅文化才更加丰富多彩。我写过一首诗,我讲六祖,“不到黄梅开正眼,慧能犹是砍柴人。”慧能不到黄梅,他不就是砍柴人一个嘛。他到了黄梅,得到了五祖的认可印证,使他一下子震烁古今中外(不光是中国,连外国也独一无二)。所以这个事情了不得。这个事情只有五祖有这个慧眼,只有六祖有这个承担,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到黄梅去,就是弘扬四、五、六祖。到河北,就是赵州、临济。我在湖北,弘扬四、五、六,提倡黄梅禅,也经过很多年。今年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到四祖寺调研,提出了“弘扬禅文化,打造大品牌”的口号,无疑对黄梅禅文化的弘扬,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您即提出“生活禅”的理念,其后每年举办夏令营,在佛教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请您为我们谈一下生活禅的理念、生活禅的推广以及这十年来您的一些经验。
净慧长老:我想,生活禅要解决的是佛教理念的问题,禅的方法问题。我们都知道佛教讲慈悲和智慧,这和我们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一些理念比较符合,现代社会就能够接受。但我又把它加以新的诠释,以觉悟人生代替智慧,以奉献人生代替慈悲,这样的口号大家更容易接受。这个口号在佛教界可以有,在社会上也可以慢慢形成为主流词汇。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如果形成社会的主流词汇,其力量和作用就比在教界要大很多,它可能会影响很多人。不管是不是真的觉悟、真的奉献,但是总有人真的觉悟,总有人真的奉献。“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是在佛教根本理念上的新的提法。
然后在修行上,我提了“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这也是一个根本理念。人们往往认为,修行就要到山林和寺院,要脱离人际关系,脱离社会实践才能修行。生活是人类活动的总和,生活就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在生活中修行,不脱离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所以“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这个理念,对于现代人来讲,提供了一条修行的捷径。我大概就做了这两件事情而已,其它所有的事情,都是为这两件事情服务。所以生活禅就是在生活中修行。这个理念可以稍微转化一下,就是在生活中念佛,在念佛中生活,也是一样的。实际上这就是理论与实践、出世与入世的紧密结合。所以生活禅基本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对佛教的理念进行新的诠释,对佛教修行的方法进行新的概括。这样,使佛教与我们现实的人生联系得更加密切,使得佛教的圣殿不至于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一个当下就可以实现的乐园。
扩展开来讲,佛教经过了中国化、大众化、现代化的三个阶段,所以注定佛教要走大众化的这条路。现代化是从太虚大师开始的,我们现在弘扬“生活禅”,还是走他的路,实际上他的路还很遥远,我们连一半都没有走到,应该说才刚刚起步。
记者:您18岁即到云门寺受具足戒,其后成为虚云老和尚侍者及传法弟子,请您给我们谈一下您对虚云老和尚的印象。虚云老和尚对您修学禅宗有着怎样的影响?
净慧长老:这个问题说起来话很长。有三件事,我回忆一下。我今年的这个形象和这三件事也有关系,今年是辛卯年,我在上一个辛卯年投奔到云门寺虚云老和尚座下,那是1951年,到今年整整六十年……所以,今年我把胡子留起来,作为纪念。纪念我这六十年,沐浴虚云老和尚法雨之恩。六十年前,我正式成为一名禅宗的僧徒,六十年前,亲历云门事件,当时我也身临其境。那个大概有50几天的事件,身临其境。也可说没有60年前的1951年亲近虚云老和尚良好的开端,也就没有60年后的今天。佛法的因缘,禅宗的因缘,以及修学的因缘,都是在1951年那个大的形势下所造成的。所以只有以感恩的心来回报我们这个时代给予的一切。
记者:早在1956年中国佛学院创立时您即入学深造,请您谈谈当时入学的情况及对当时几位教界高僧大德的印象(周叔迦居士、明真法师、正果法师等)。
净慧长老:1956年9月份,我到中国佛学院读书。你们江苏的明学法师,当时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也住在一个宿舍。当时我们的宿舍是四个人一间,明学法师是我们的老大哥。从1956年到今年也有55年了。1951年到云门寺亲近虚云老和尚,算是一件大事;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到中国佛学院读书。正是由于这两件大事,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前途和命运。
这个当中,使我最受感动的几位老前辈,是我终生学习的表率。比如我们的院长喜饶嘉措大师,虽然平时和他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一年都要来作几次报告,发现他信仰虔诚、学识渊博、为人亲和,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
其次就是赵朴老,谦谦君子,才华横溢。他对佛教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半个世纪,执掌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务,经历了解放初期的各种运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风波,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20多年的时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如果没有赵朴老,不但是中国佛教没有现在这个面貌,甚至整个中国宗教,都没有现在这个面貌。他不仅是我们佛教界的一位领袖,也是整个宗教界的领袖,他也为宗教界说了很多话,他是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最受尊敬的一位老人。所以我在佛学院接受他的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又在中国佛协工作了一段时间。有很多东西,是从他老人家身上学到的,并且受用不尽。
另外就是周叔迦先生及其公子周绍良先生。周叔迦先生是我的老师,周绍良先生亦师亦友,这两位先生都对我有很多提携。我到河北来,如果没有周绍良先生的催促、提携,我是不可能成行的。他一直提携我,他说,河北如此盛情邀请,你不去,辜负人家了。另外,你是出家人,还是有个寺院才好。佛教协会毕竟是一个团体组织,不是一个寺院。所以经周老一再提醒,再加上赵朴老的督促,我于1988年1月正式接手河北佛教的工作。当时周老是佛协的秘书长,所以成就我到河北的因缘。明真法师、正果法师都是非常慈悲的人。还有法尊法师,学问特别渊博,我们在一起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伺候他们的生活起居。1979年从乡下回到北京,他们都是老人了。我当时四十多岁,还可以干活。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法师、老前辈。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一个出家人的心态、度量,待人接物的方法。解放之后,“文革”期间,他们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他们心态平稳,无悔无怨,非常了不起。虽然我也当了十五年的右派,但是和这些老法师一比,他们都是大德高僧,我不过是个小萝卜丁。所以有一点点委屈,心里也就慢慢地平和了。他们的言教身教、感染力,我是从心里佩服这些人,而不是在嘴巴上,从心眼里就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说的话我们就听。那时候,我们做学生很有意思,尽管是在政治运动中,我们也是经常亲近这些老师。所以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良师益友,佛教里讲善知识,离不开善知识的成就。当然,我们今天的一个和尚能够成长起来,也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栽培成就,各种时节因缘的成就,善知识的成就,才会有今天的佛教。
虽然他们都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精神及他们所培养的学生,还在继续着他们的事业。
记者:您曾负责《法音》编辑工作多年,又创办《禅》、《正觉》等多种佛教期刊,在主编佛教期刊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您认为办好佛教期刊要注意哪些要点。
净慧长老:办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在《法音》编辑部22年。办刊,要说有什么经验,好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很奇怪。但是你要是把刊物拿到手里一看,好像又有些感觉。我想,办刊物,特别我们佛教的刊物,不能太学术化,不能太政治化。太学术化,脱离了大众;太政治化,也脱离了我们的本职工作。重要的,作为一个会刊,有一些政治性的内容要报道。比如我就听到人们的一些议论,说这个刊全是文件,全是报纸上有的,都不讲佛教的事情。我想这些来自读者的声音,是我们办好一个佛教刊物应该引起注意的事情。从刊物本身来讲,首先传播的知识应该是可靠的,知识的可靠性,文章的可读性,内容的正确性,内容上不能有误导;然后,刊物整体的编排,文章的形式、文笔,都要具有时代性。没有时代性,和读者格格不入;具有时代性又不能太花俏,有时代性又要有佛教刊物的庄严性。我想把这几点做好了,这个佛教刊物就基本上成为了一本可读的刊物。
现在佛教的刊物几百种,读者对大部分刊物不满意,因为都在低水平上面徘徊、轮回,都是文章的转抄,都是文摘性质的。大概目前大家比较喜欢看的是《禅》。可读性比较强,针对性比较强,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对修行也有一些作用。对《禅》的评价还可以,其它的刊物能够赢得读者好评的实在太少,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太花俏了不行,太突出个人了不行,没有主题不行,没有新的理念也不行。刊物很难办,特别是作为一个会刊,更难办。
我觉得,如果佛教刊物也承担了弘法的任务,怎么做到弘法的大众化,也应该是其中的一条。我们《禅》刊每期发行12万份,而有些刊物的发行量年年在萎缩,这就成问题了。
因此,办杂志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要一边办,一边探索,在怎样大众化上面下功夫。在定价方面,不宜太高,如果能免费结缘更好。另外,就是办刊一定要请专业的美编。